“我是把《安顺城记》看成是人生学术工程的最后一个总结,这不仅是我自己学术的需求,同时还有一种感情的追求。我想通过编写《安顺城记》,来作为对贵州这块土地,以及养育我的父老乡亲的一个回报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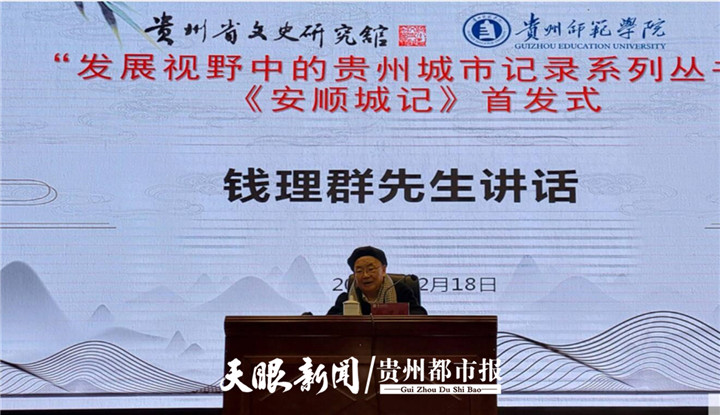
钱理群先生以个人出资的方式,向贵州各市州的图书馆和学校捐赠1000套《安顺城记》
1960年,钱理群先生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任教,并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18年,之后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,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。安顺是承载了钱先生18年生命历程的第二故乡,正是源于他对第二故乡的深情和眷恋,才有了《安顺城记》的出版与面世。现场,钱先生分享了该书产生的灵感来源、编纂特点、学术价值,以及个人对贵州的深厚感情。
从一个人的梦,变成一群人的梦
“谈起《安顺城记》,真是百感交集,勾起了很多很多的回忆。”当天的《安顺城记》首发式上,钱理群先生发言的第一句话,就蕴藏着深深的感情。
他回忆说,自己晚年有一个习惯,就是每天醒后半个小时,会静静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,想一个个奇奇怪怪的关于学术研究、写作和编书的计划。《安顺城记》这样的学术大工程的缘起,就是16年前,自己所做的一个梦。
“2004年11月20日,我躺在床上想自己和整个学术届,以及历史研究,包括地方志的写作,觉得按照现在的老路走下去,实在没劲。”钱老解释,之所以觉得没劲,是深感现在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三大问题:有史事而无人物;有大人物而无小人物;有人物的外在事功而忽视了人的内心世界。
“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,今天包括历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,越来越知识化、技术化、体制化,缺少了人文关怀,没有人、人的心灵、人的生命气息。这样的学术、史学,只能增进知识,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,心灵的触动,生命的感悟。”
钱老说,这样想的时候,突然就想到了《史记》,并想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体例,来写贵州历史,写一部《安顺城记》。“说实话,想到这个鬼点子,我真是兴奋极了。”他说,自己于是便迫不及待地找安顺学者杜应国商量,“他也很兴奋,并拉了一个构想脉络”。
然而,第一次把这一梦想公诸于世,其实是2007年。当时,钱老在一篇《土地里长出来的散文》的文章里,通过司马迁编写《史记》的故事,动情而又意味深长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,并提醒贵州学友:不必、也不可妄自菲薄,小城里自有大文章,我们所做的工作对于当今中国,乃至于对世界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,就是要做当代的司马迁。
之后,他于2008年起,先后找到贵州学者戴明贤与袁本良两先生商量,大家都非常兴奋。这样,这个梦就由两人的梦变成了4个人的梦。后来又找到学者顾久先生,对方也欣然同意加入,这样就又成了5个人的梦。再后来,又得到省文史馆、安顺市社科联等单位的支持,于是一个民间修书的学术大工程就成了一群人的梦,并落地在贵州。

钱理群先生为88038威尼斯印山书院及省文史馆“山骨讲堂”揭牌
第二故乡的好人,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
学界关于钱理群先生的一则轶事是,他退休后很多人都不见,但除了贵州人;他很多地方都不去,但除了贵州。果断的话语背后,是他对第二故乡割之不断的眷恋和深情。
“我对贵州对我的影响有4个概括,第一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,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;第二是和贵州真人的交往,培育了我的堂吉诃德气;第三是文革中的摸爬滚打,练就了我的现实关怀、民间关怀和底层眼光;第四是在贵州的18年的潜心读书,奠定了我的学术和我治学的底气……”
四条总结,被钱老概括成一句话:“可以说,我的一切,如果不来贵州,那将是另外一个钱理群。”他说,正因如此,不管今年多么严寒,自己一定要来参加《安顺城记》的首发式,并把它看作晚年所做的一件最大的事情。“他不仅凝聚着我的历史观、方法论、追求,并且是我的学术和生命真正的落地生根,这是我一生最好的归宿。”
正是这样一份深情,钱先生在2012年10月25日召开的《安顺城记》首次工作会上,提出一个口号:“我的第二故乡的好人,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,写一部我们自己认可的《安顺城记》。”他说,这是一件泽被后世、功德无量的事,因此当时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。
两年后的又一次工作会上,钱老做了“为我们自己、为未来的读者写作”的讲话。他解释,这里的“我们”实际上包括了6代人,这6代人共同经历了共和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,也是个人命运的巨大的转折,在这一过程中,大家形成了某种共同的或者接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,如多少都有一点理想主义、有一点社会承担意识、一点对本土的情感和责任。因此,大家尽管历经沧桑,彼此的现在状况也有很大不同,但仍然能够聚集起来编写《安顺城记》。
“对我们这一群人来说,编写《安顺城记》不仅是一个学术工程,更是一份情感的投入,一个生命的投入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友情的纪念,我们用一本大家共同认可的书来铭记我们这几十年或者几年的友谊,成为一个友谊的纪念碑,这里蕴含着生命的诗意。我们最后玩一次浪漫主义,再做一次梦。”钱老说。
他感叹道,之所以说是最后一次,是以后恐怕很难集中这么多人、花这么大精力、下这么多的笨功夫做一件事了。自己准备以这部书来结束个人的学术生活,而参与这部书和组织写作、编辑的朋友们,以后恐怕也很难有机会再做这样的民间修书,而今天、以后年轻人,大概也未必有兴趣做这样的事情了。

钱理群先生为贵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揭牌
从这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生命的永恒
这样一部从萌发想法到出版历时16年的作品,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呢?钱老现场进行了总结,他说:第一,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,提出了多民族共同创造,乡绅与乡民共同创造的多元化的历史观;第二,打破以汉族为中心的惯常做法,把少数民族的历史、甚至少数民族的创世梦写进去;第三,灵活变通了《史记》体例和结构,将纪传体与边缘体、专识与通识有机结合;第四,继承《史记》传统,强调表达的文学性,强调历史细节,强调生命气息,强调文学的语言,包括方言的运用。

“我的总结,这是一部既有继承又有创造的、真正的现代地方史。”钱老说。
“尽管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强调传统文化、地方文化、乡土文化研究,但像我们这样扎扎实实干的并不多。我强调我们要有自信心,我期待《安顺城记》能够对当下的中国学术界,以至于在国际上产生影响。”钱老说,大概很少有这样既有自己独创的思路,在学术上有很大创新性、又承接下来,积8年之功做的这样一个大学术工程,因此不要老觉得安顺、在贵州边远地区有一种自卑感,因为至少在地方史研究上,我们是应该有信心的。
“我这个人喜欢做梦,《安顺城记》出版,梦完成了,我又开始做新的梦。”钱老说,自己梦想在《安顺城记》的基础上,可以做更深入更全面的学术研究,因此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些学术论文,重新构建安顺学,甚至构建贵州学。另外,还可以考虑用现代的最新的传播工具,把《安顺城记》转化成一种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,更好地向年轻人传播安顺和贵州的历史文化。
“多年前在戴明贤先生的倡导下,大家写了很多安顺文化的散文,当时称之为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。现在,《安顺城记》完全可以看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,这种从土地里长出来历史最接地气,和生长在土地上的父老乡亲,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命血肉相连,可以从这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生命的永恒。”钱老说。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赵毫
编辑 帅宗林